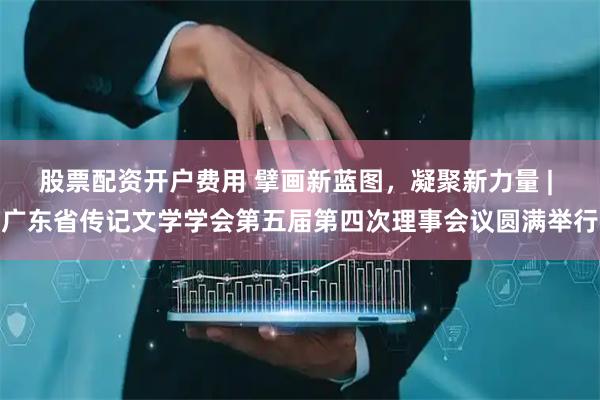“喂,北京民政部吗?……我们刚收到一张写着‘革命烈士’的大红证书!”1983年5月10日早晨,杭州老宅里电话刚放下,邵飘萍的孙子邵澄的手依旧微微颤抖。他万万没有想到,去世近六十年的祖父,竟在今日等来了国家最正式的褒扬。而紧随其后的第二通来电股票配资开户费用,更是让全家陷入长久的沉默——中央已批示,邵飘萍遗骨可移入八宝山革命公墓,择日执行。

消息不胫而走,那天傍晚,婺州公园的铜像旁,几个新闻老前辈相约而来,他们提到毛泽东生前的嘱托:“总得给老邵一个交代。”这并非客套。早在1949年北平解放前夕,毛泽东就亲笔批示“追认邵飘萍为革命烈士,并照顾其眷属”。只是战后百事待举,手续一拖再拖,直到八十年代才最终落定。邵氏后人确认批件时,工作人员特意提醒:“备注栏里存着一行字——‘根据毛主席生前意见办理’。”
时间拨回到1936年7月,延安窑洞里,毛泽东接受斯诺采访。他开口就谈到几个名字:李大钊、陈独秀、杨昌济,还有邵飘萍。“那位教我新闻写作的自由主义者,被张作霖枪决十年了。”毛泽东抬头望着窑顶,声音压得极低。人们只知道他敬重李大钊,却少有人注意,那位以“铁肩担道义,辣手著文章”自励的报人,同样深刻影响了这位后来改变中国的领导人。

1918年秋,22岁的毛泽东初到北大,身份只是图书馆助理员。肃穆的图书馆外,新闻学研究会的招募启事贴在灰墙上,一排黑体字非常醒目。李大钊看出了毛泽东对新闻的兴致,便带他去旁听邵飘萍的课。那是毛泽东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“公开发言”,面对满堂学生,他阐释舆论与民意的关系。有几名本科生不服气,窃窃私语:“一个打工的也敢来教室指点江山?”坐在讲台旁的邵飘萍却摆摆手:“观点对错不在身份,我看这位毛同学说得有理。”
从那以后,两人私下往来频繁。邵家的客厅里常能见到一个身形高大的湖南青年,双眼通红却依旧聚精会神地听课。有一次,邵飘萍半睡半醒,听见木门轻响,他干脆起身拿出《新闻学大意》手稿递过去,说:“小毛,你看看这几页,帮我挑错。”毛泽东读完直言:“先生自称自由主义者,却处处关照底层,这股劲头我佩服。”一句话让邵飘萍哈哈大笑:“铁肩才配自由!”

1926年4月,北平春寒犹在。因为连续发表揭露奉系军阀黑幕的社论,《京报》主笔邵飘萍被捕。狱中他拒绝供出同道,胫骨被打断,仍高呼“新闻自由万岁”。4月26日拂晓,枪声响起,年仅四十岁的他倒在菜市口刑场。那一夜,远在长沙的毛泽东手握电报,沉默到天亮。后来有人回忆,他只说了一句:“我们会继续写下去”。
此后十余年,毛泽东笔不停挥。《湘江评论》《政治周报》《红色中华》《新华社广播稿》……文字如匕首,直指国民党要害。1948年10月,傅作义十万大军南下意图偷袭西柏坡,解放军主力尚在前线。毛泽东却接连四天发布新闻电讯,把敌军行军路线、指挥官姓名、企图目的一一曝光。傅作义惊慌失措,最终撤回保定。西柏坡“空城计”能奏效,背后少不了当年邵飘萍那句“辣手著文章”的影子。
建国后,毛泽东忙于政务,却仍惦记旧事。1949年底,他特地让秘书携带布匹、粮票与慰问金去看望邵夫人汤修慧。临行前他叮嘱:“她是师母,好生照顾。”汤修慧听闻毛泽东口信,不禁潸然。那年冬天,她给儿女写信:“记住啊,你们的父亲不是孤魂,他有学生记着。”

1958年1月,毛泽东同人民日报负责同志谈话,再次提到邵飘萍。他强调记者应当“保持冷静与独立”,不要随风摇摆。那番话今天仍被新闻学院当作范本,而其源头,就在半个世纪前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小教室里。
1976年9月,毛泽东病重。晚辈问他还有何未了心愿,他闭目片刻:“邵飘萍的事,办到哪一步了?”当时移墓程序尚未完成,文件层层流转。对话被警卫员悄悄记下,成为邵氏家族后来得知“幕后推手”的依据。

于是才有了1983年那张烈士证明。民政部档案显示,文件批号开在1977年,但手续真正完备却拖至1982年底,足见过程曲折。翌年9月24日,邵飘萍棺木由家属陪同,悄然送抵北京八宝山。石阶静默,苍松肃立,红绸掀开一瞬,孙辈忍不住失声痛哭。工作人员低声提醒:“请节哀,这是荣誉,也是责任。”
1986年3月2日,96岁的汤修慧在杭州病逝,中央批准其骨灰与丈夫合葬。入墓那天,她的曾孙邵槐牵着尚牙牙学语的女儿站在碑前,孩子不知肃穆,只问:“太爷爷有什么了不起?”邵槐蹲下,说:“因为他写东西不怕死。”短短八个字,道出了中国新闻史上一段血与火的注脚。

今天回望,邵飘萍之被公认为烈士,并非单因他是中共秘密党员,更因为他用笔墨撬动了时代。毛泽东以学生身份承继这套方法,将舆论武器化,最终改变战局。1983年那纸证书,不过是对二人精神关联的一次官方确认。邵飘萍已去九十五年,他的“铁肩”却仍在报端、在屏幕、在每一次针砭时弊的文字中延续。
美嘉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